摘自2003年8月22日《北京青年报》
妻子眼中的袁苑
“我是狗袁苑啊!”
虽然袁苑的生肖属相是蛇,但我说他属狗更合适!
“非典时期”,袁苑打电话给他的恩师郭宝昌导演问候,郭导演听说“我是圆圆”后问,“你是哪个圆圆?”“我是狗袁苑啊!”“啊呀,狗袁苑!”郭宝昌一下就从众多的“圆圆”中区分出来了。
“狗袁苑”外号可不是我给他起的,是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的馈赠。他单刀直入从来不加掩饰地表达,得罪过不少人。狗急的脾气,炮筒子、直肠子,动辄爱发火,发完火就没事儿了,深知他脾气禀性的哥们儿就说:“这袁苑,属狗的!”
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是他最大的缺点。一次在一个民营影视大赛上,作为嘉宾的袁苑应邀讲话,前面几位都客气、委婉地预祝前来参赛的各地选手成功!甚至还有的展望道:“很有可能从这里走出新的巩俐和姜文!”但袁苑上来却说:“估计你们这上千人里最后能出来一个有点儿小名气的就不错了!”他认为不能无根据地让孩子们盲目乐观地做明星梦,只有直言不讳地先讲清演艺事业的艰难,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面对失败的打击。
我理解他的苦心,袁苑当初进入影视圈的道路很不平坦,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无力在影视圈里帮助他找到靠山,一切只能靠个人奋斗。为了接近这个圈子,他必须和其他外来者一样,调动所有的潜力和资源,比如帮助肯引荐入门的人寻找紧俏物资、设法解决对方遇到的困难,有时候甚至还得出卖一定的体力……
火暴性格的袁苑,在委曲求全的日子,偶尔发发狗脾气,既是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也是唤起关注的必要步骤。其实呀,袁苑越是在内心比较虚弱之际,才越是爆发狗脾气的时候。
■我始终认为袁苑勤劳、勇敢但缺少智慧
我与袁苑共同生活已经整整18周年了。我们是1984年在甘肃拍摄《韩海潮》时相识的。第一次见到他,我感觉他相貌蛮凶的,用我们上海话就是———吓人捣怪的。可实际接触后,我才发现不能单纯地以貌取人。别看他说话大声大气,浓眉动不动就竖立起来,两只大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怪吓人,可他很真实、诚恳,不当面奉承你,却直截了当指出你的不足。他待人透明和率直,虽说给他带来过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但却赢得了我的芳心,我们在一起说笑很轻松、很愉快,心理上不用设防。
当时拍摄一场戏要用航拍,需要我们俩人在沙漠上相依地走很长的一段路。我们按照导演的要求,义无反顾地在沙漠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没想到,走了两个多小时,太阳已经失去余威,气温开始寒冷了,还没有接到“停”的指令。因为头上始终没有飞机的轰鸣,袁苑估计应该拍完了,就擅自决定“咱们别傻走了”。后来才知道,飞机出了故障,一直在紧急抢修。沙漠气候一天三变,温度骤降后,狂放随即而来。我们瑟瑟发抖地等待剧组救援,袁苑就站在迎风一面,把我挡在他的身后。从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信任他!这样的男人是靠得住的、是负责任的。一个男人可以不英俊倜傥,但不能没有宽阔的襟怀,他可以不太智慧,但绝不能缺少诚实和毅力。
我始终认为袁苑勤劳、勇敢但缺少智慧。他不是那种很有灵气的聪明人,可他执着、脚踏实地、肯埋头苦干,做任何一件事都善始善终,孜孜不倦,只要他做了,就一定尽最大努力坚持做完和做好。
他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耐性,有时真让我困惑不解。火暴的狗脾气,凡事却总要丁是丁,卯是卯。袁苑订了不少报刊,《北京青年报》肯定是首选,《小说月报》、《读者文摘》和《中篇小说选刊》等等七八份。他每版必读、每篇必看,十分认真。读后从不乱扔,看完的报纸按每版的顺序依次排列,杂志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茶几下,每到月底一并撤出,运到储藏室保存起来。那一丝不苟的态度,就像一个尽职的图书资料管理员。
他说这是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习惯。在济南三年的通信兵生涯里,为了躲避晨练,袁苑自告奋勇,主动承担全班的卫生整理工作。在晨练和叠被的选择中,他更喜欢后者。如今,他把这光荣传统带到我们家里发扬光大了。他不允许房间里有半点儿凌乱和纷杂。
很有耐心的袁苑,在吃的方面也是如此,他特别喜欢吃螃蟹,从来不畏惧繁琐。有一次请朋友做客,我蒸了十多只大螃蟹,不想人家客人嫌脏怕麻烦不肯吃,结果几乎让袁苑全部独占,他有条不紊地拆卸下螃蟹的肢体,颇有技巧地向我们传授经验,我们只是笑着看看,都怕弄得满手腥。“哼,吃都嫌麻烦!”很快,他的桌前就摊满了螃蟹的残肢断臂。客人惊叹:“袁苑真有耐心!”
空啤酒瓶子,想必谁家都是往阳台的角落信手一扔。可袁苑不仅把每只酒瓶井然有序地一排排码放,竟然还把酒瓶上的每张标签都扭朝一个方向,好像是等待检阅的列兵!在家务分工上,细活一般都由他负责,我只配做一些粗活。
■“我们的女儿要被强盗掠走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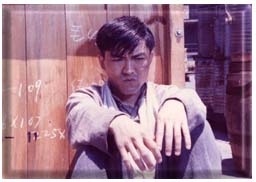
他乍看形象粗糙,不想却藏着内秀。当初带他回上海见我的父母时,父母的反应很惊讶,妈妈把我拉至一旁,悄声问道:“这模样吓人捣怪的,脾气一定很凶吧?”我摇摇头,妈妈还是将信将疑。
爸爸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开玩笑道:“看来,我们的女儿要被强盗掠走了!”
可谁又能想到,患癌症的父亲是在这个“强盗”的护理下,走完了人生难熬的最后历程。当时我在外地拍戏,连回来看一眼都不可能,更何况床前伺候。哥哥一家远在日本大阪,鞭长莫及。袁苑只身前往上海,替我尽了女儿的孝道。从喂水、喂药到擦拭身体,袁苑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给父亲翻身时,父亲只同意“强盗”一个人来操作,任何人他都坚决反对。事后,妈妈说:“袁苑这孩子真是太好了!若换了儿子来,也未必能这样周到、细致。翻身时,总要把你爸爸的衣服全部抻平,还把床单也抻平,生怕有一点点硌着。唉!真难为他了!”
追悼会上,妈妈代表我们全家给袁苑深鞠躬,所有到会的来宾都夸我找了个好丈夫。
我没有说什么,当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就亲眼目睹了他对老人的孝心。我第一次去找他,是在医院里。19年过去了,但我对第一次去医院的印象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的母亲身患绝症,吞咽已非常困难,每天却要服大量的中成药。袁苑伏在床边,一面跟母亲聊天,一面分割大药丸。每个大药丸,至少要分掰成二十来个米粒状的小丸,他每天都这样一个个耐心地分割。也就是那一刻,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你开起车来跟你的属相真一样!”
婚后,我渐渐地放弃了表演。女性演员最大的障碍就是年龄,当电视剧风起云涌之际,我却失去了再担纲主演的最佳年龄期。袁苑理解我的苦恼,他劝我说,不演戏没关系,但千万别一蹶不振。他认为我的人生之路有着多种选择。“你在学校时,作文就总是在全校被巡回展览,至今你的那些同学还记得呢。你可以尝试着从台前转到幕后,把精力和重点转向编剧和制片呀。”
在袁苑的提示下,我开始搞专题片。经过一定的积累后,我又开始剧本的策划和编写,开始积累制片发行、剧本策划的经验。考虑到有一段时间,外貌粗犷、棱角分明的男演员不再吃香,袁苑也及时调整自己的航线,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陆续与多家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夺命惊魂上海滩》等一系列影片。
不过,袁苑那时的心情并不好,虽然他能够把制片工作细针密缕地做好,但他更喜欢的还是镜头前的表演。我们那时总是相互安慰和鼓励,面对许多同时代的演员在无望的行进中悄悄地隐退或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我劝他:你的表演和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你的艺术生命力还没有走到尽头。
袁苑属于今夜想起来,明天天一亮起床就实干的人。他不让自己沉溺于虚无的幻想之中,而是实实在在地行动。比如开始角色转移,不再继续饰演年轻的小伙子,而是面对中年人的形象。比如,尝试饰演古装戏,一改以往现代“坏蛋”较为单一的模式。自强不息的下岗工人或者富于喜剧色彩的“山大王”,图谋不轨的珠宝商或杀人放火抢银行的大盗,他一个接一个地演。我觉得他太累了,就劝他适当地可以拒绝一些角色,毕竟已经50岁的人了。可他满不在乎,他高兴,每塑造一个新角色,他都乐呵呵地给我讲来讲去。
除看电视、读书外,他的业余喜好就是玩电脑,可惜不会发电子邮件,对扑克牌特别投入,乐此不疲。还好,他没有通宵达旦与人相约打麻将的嗜好,连烟酒也不沾。只是遇到聚会,有朋友强迫他尽兴,他往往不好意思拒绝。我不会陪他应酬的,因为加入我,他们反而不能尽兴高谈畅饮。他开车很猛,我甚至都不敢坐他的车,他总嫌前面的车辆速度太慢,频频超车,我感觉就像一条行进的蛇,一闪一闪地突然抢在人家前面。
“你慢点儿成不成?多危险啊!”任我在一旁尖叫,他依旧我行我素。“你开起车来跟你的属相真一样!”我气愤地说。
袁苑反诉
吴颖和她的父母也深受脸谱化的毒害,最初总把我往坏人堆里算。这也就难怪导演一有反面人物就想到我了。
关于我的狗脾气,我得说两句,狗被主人拴着失去自由,尤其是农村的狗,主人想起来喂两口,一忙就忘了,可它对待主人永远是忠心耿耿。有时主人还错怪和伤害它。我认为狗是世界上最凄凉的动物!
我比较烦吴颖像保姆似的管我,她总认为她的意见都对,其实是外行管理内行。比如说我开车符合我的属相,完全是她的无知。变线必须要加速,若是听从她的指示,慢慢腾腾地跟牛似的移过去,那不出事故才怪了呢!